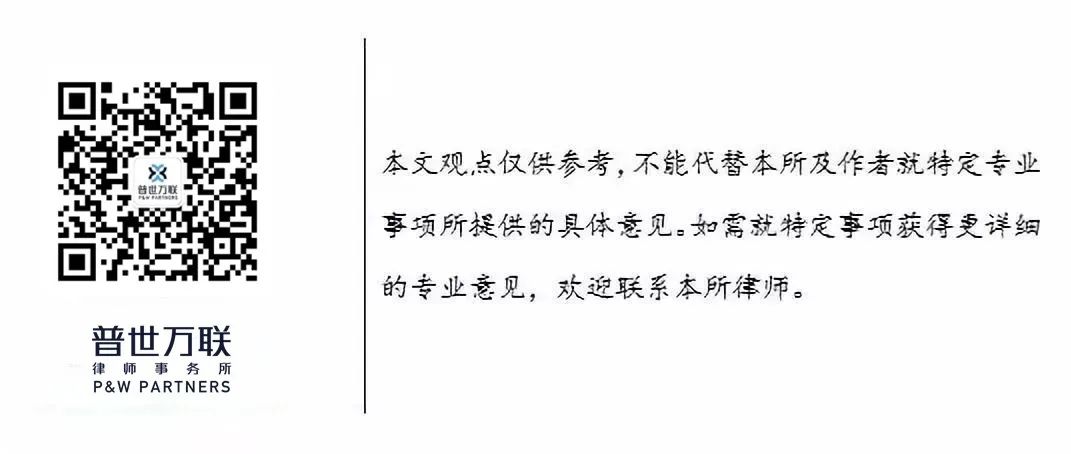文 | 秦卓然律师
当前,上海市本轮新冠疫情目前已得到有效控制,城市生产生活正在逐步恢复,各类企业也正在分类有序复产复工。但是,由于长期处于疫情防控状态导致各项工作无法正常推进,企业间难免产生各类合同纠纷。而如何确定合同履行地、合法合理适用管辖规则是首先遇到的重点问题。近期,笔者与团队在处理一起合同纠纷案件管辖权异议的过程中,就遇到了原、被告双方对于合同履行地的确定产生了极大争议的情况。笔者本次就针对这一问题与大家进行简要探讨。
A市的甲公司(我方代理)与B市的乙公司签订《某产品技术服务协议》,约定由甲公司向乙公司提供产品安装及售后服务,乙公司据此向甲公司支付技术服务费用。合同签订后,乙公司向甲公司支付了预付款,甲公司亦向乙公司提供了上述技术服务,但由于后续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产生分歧,乙公司遂以甲公司未履行技术服务义务为由,要求甲公司退还已支付的预付款。乙公司认为,因其诉讼请求为要求甲公司退还预付款,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故合同履行地应确定为乙公司所在的B市,据此,乙公司向B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团队接受甲公司委托后,代表被告方向B市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理由为:本案中,甲公司认为自身已履行技术服务义务,但乙公司认为甲公司未履行技术服务义务,虽然乙公司的诉请系要求甲公司退还技术服务费,但本案争议标的并非“给付货币”,而系“其他标的”,不应适用“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确定乙公司所在的B市为合同履行地,而应由被告所在地A市人民法院管辖。
上述管辖权异议递交后,B市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申请。随后,我方不服裁定提出上诉,上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就确定管辖而言,讼争法律关系的性质应以起诉人的诉讼请求和起诉事由为基础,结合起诉证据予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结合乙公司起诉事由及请求,本案诉讼请求并非争议标的,而本案争议标的也并非给付货币的合同义务,故本案争议标的为“其他标的”。据此,上级人民法院裁定本案移送A市人民法院管辖。
在本团队办理的上述案件中,我方之所以能够在本案管辖权异议中获得胜利,关键在于对合同履行地如何确定的把握,以及对《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理解。事实上,在我国的审判实务中,人民法院在诸多案件的管辖方面均对上述条文的适用进行过明确说明。曾有人民法院的审判员向笔者表示:在合同纠纷中,不能因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付钱就直接认为案件的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应当根据原告的请求权基础以及双方法律关系并结合案件证据去判断。
在已生效的判决中,人民法院在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案件中涉及的上述问题进行了阐述。
例如,在(2021)浙07民辖终164号案件中,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众所周知,标的指合同当事人双方之间存在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也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本案的标的为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具体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销售货物,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的法律关系。这里的货款不等于单纯的货币,一审裁定将本案标的简单归结为“给付货币”显然偏离了“标的”的含义。本案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支付货款及利息损失”。且不论被上诉人也存在违约问题,仅其要求支付货款及利息损失的请求而言,显然包含了追究买卖合同产生的违约责任,承担利息的违约责任必然用金钱来承担,但不能以此简单归结为“给付货币”。适用“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是指案件本身给付货币,比较典型的如民间借贷合同和汇款错误的不当得利等债。从一审法院案由来看,本案的标的为买卖合同关系,应当属于司法解释第二款中“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规定的情形。
又如,在(2021)沪02民终741号案件中,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上诉人主张被起诉人赔偿经济损失等费用,其诉状主张的货币给付责任属合同责任范畴,并非合同标的,故不能将其认定为接收货币方。本案争议标的系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被起诉人住所地即为合同履行地。
再如,在(2021)沪73民辖终85号案件中,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涉案协议第十条虽约定“双方可就争议事项协议履行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但未对协议履行地做出明确约定,而被上诉人在本案中起诉的是要求解除涉案协议、返还加盟费并赔偿损失,该诉请所指向的合同义务系上诉人应履行涉案协议的业务指导、协助支持、提供信息等义务,故应依照前述条文中的“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法院。
通过上述案件以及人民法院的裁判观点可见,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二款时,应当结合诉讼请求、双方法律关系、合同条款等具体案件情况去理解,而不能仅仅因为原告诉讼请求的内容是要求被告付钱,就简单粗暴地认为“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并将“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确定为合同履行地。
首先,从性质来看,《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系对《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合同纠纷管辖规定相对应的补充解释,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的一般管辖原则。
通过前文人民法院的案例不难看出,若要在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对此,学界曾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此处的“争议标的”系原告提出诉讼请求所对应的被告应承担的义务,也就是用原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来推定“争议标的”指向。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此处的“争议标的”应理解为根据涉案合同类型或性质所推定出的主要或特征义务。
根据已有的相关案例,笔者个人倾向性认为,目前的司法实务中对《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理解倾向于以第一种观点为基础,兼顾合同性质、内容等案件具体特征进行综合判定。例如,本文所举的几个案例中,人民法院在裁判时指出,原告在诉讼请求中要求被告支付货款、承担利息、赔偿损失等均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给付货币”。由此可见,在目前的实务中仍存在的直接根据诉讼请求中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钱款的内容就简单粗暴地将案件推定为“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做法,是由于对《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片面理解而产生的偏差。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系由于未充分理解“争议标的”的含义,且并未认识到要求支付钱款与“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之前存在的根本差别。
最后,笔者认为,当案件符合能够适用“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这一前提时,《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所述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系法律规定的自然人或法人住所,即此处对“所在地”的认定应当根据法定而不是合同约定。例如,很多合同在订立时,载明的当事人地址与其法定住所并不一致。此时,即便合同约定当事人的地址以合同条款为准,笔者个人认为,在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时,对“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的认定也应当以当事人的法定住所为准。
联系我们
微博:普世万联律频道
电话:021-52988666
传真:021-62317688
官网:www.pushiwanlian.com
邮箱:pushi@pushiwanlian.com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娄山关路523号金虹桥国际中心I座3层
邮编:200051